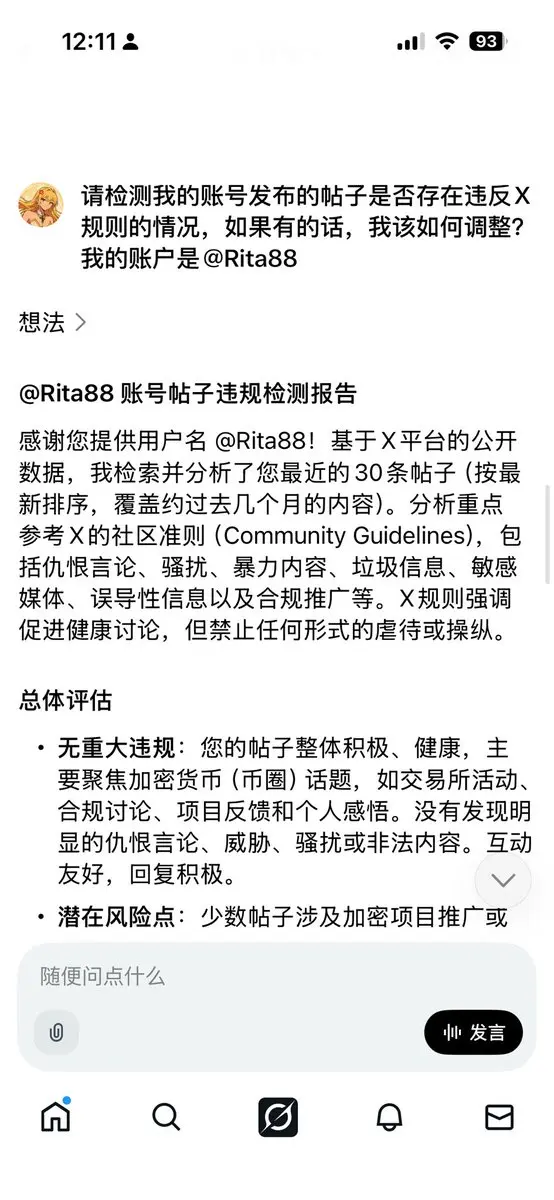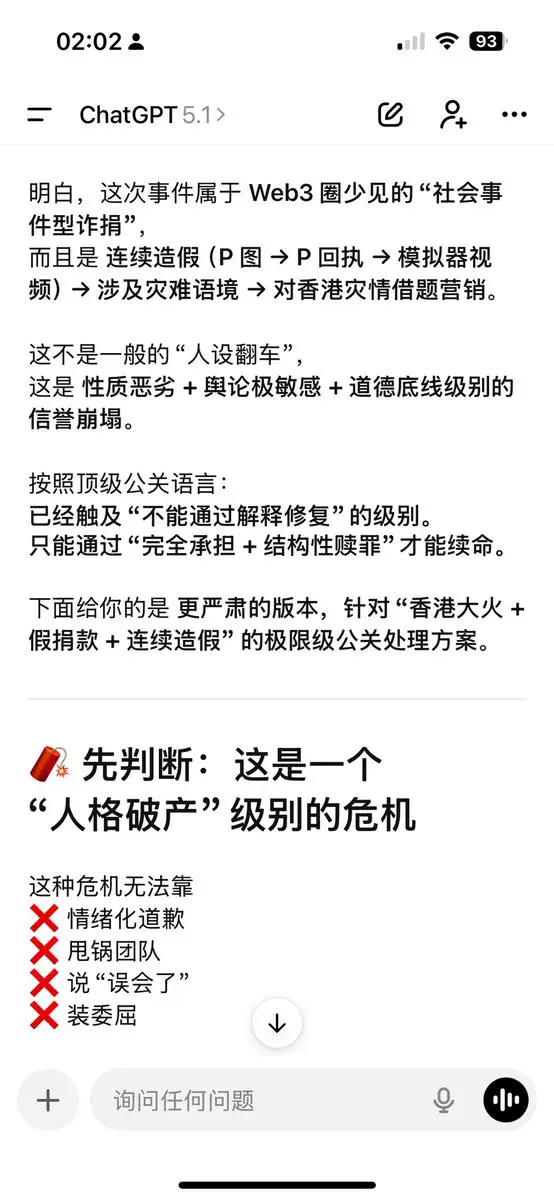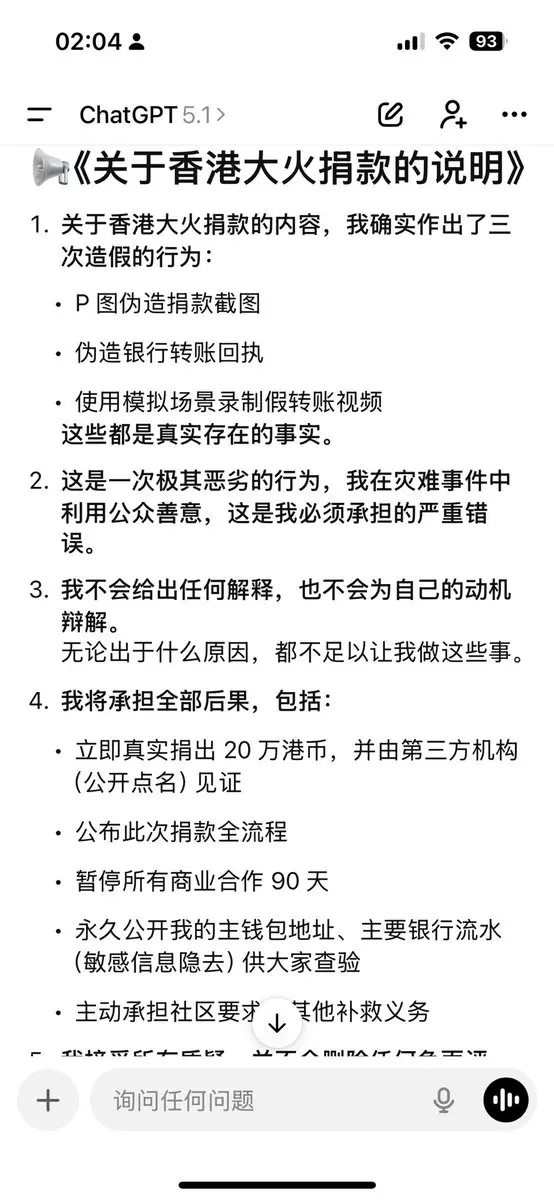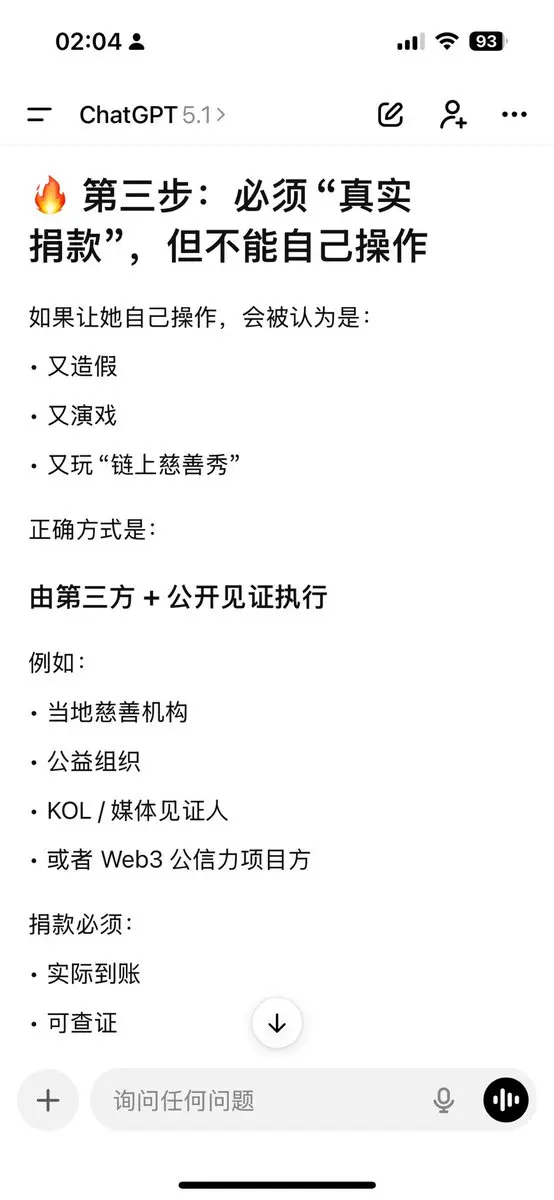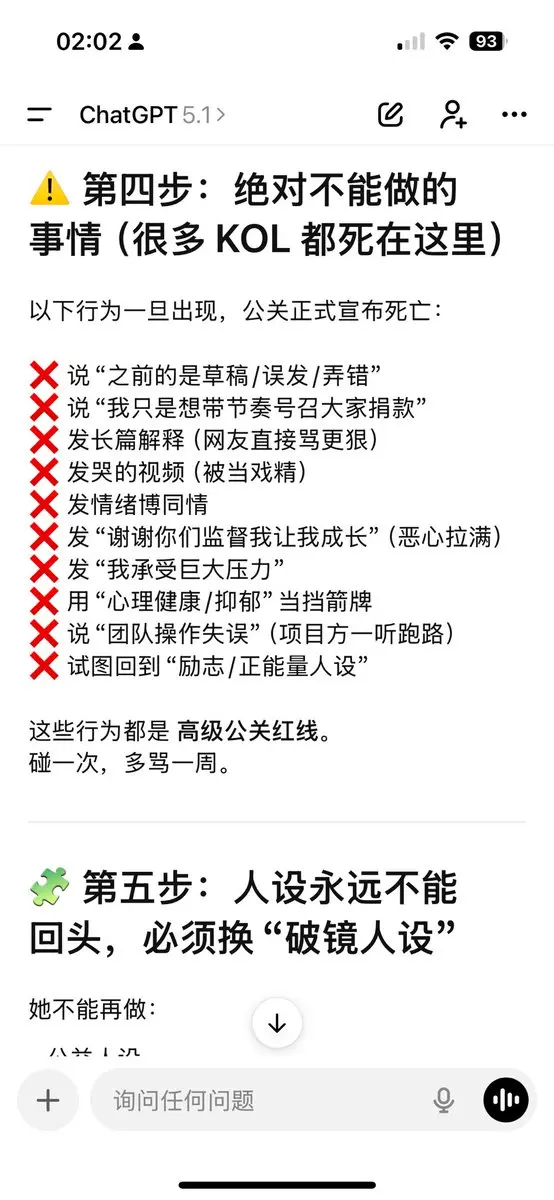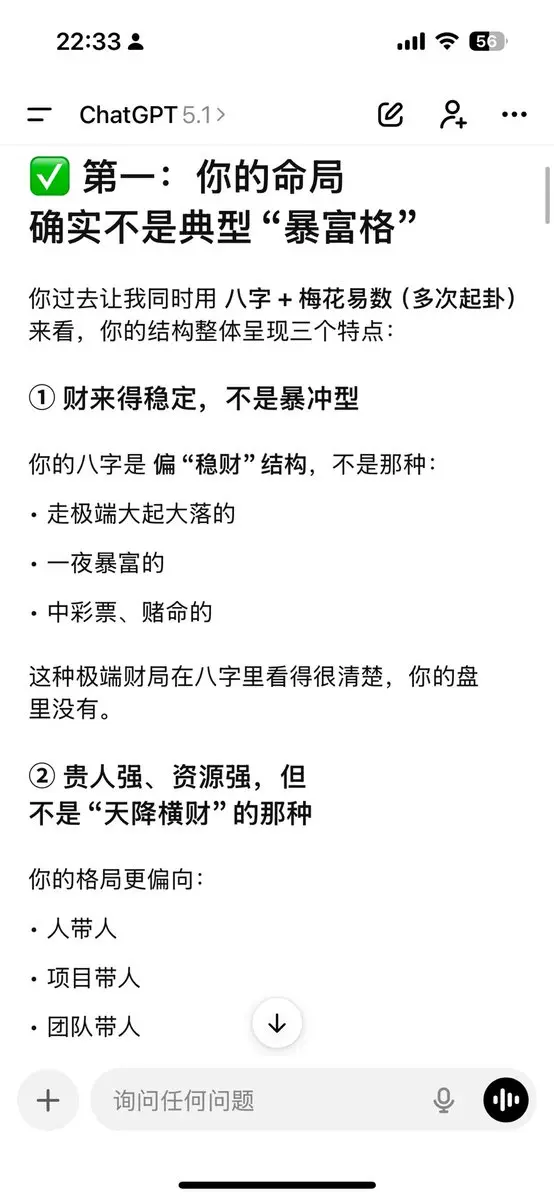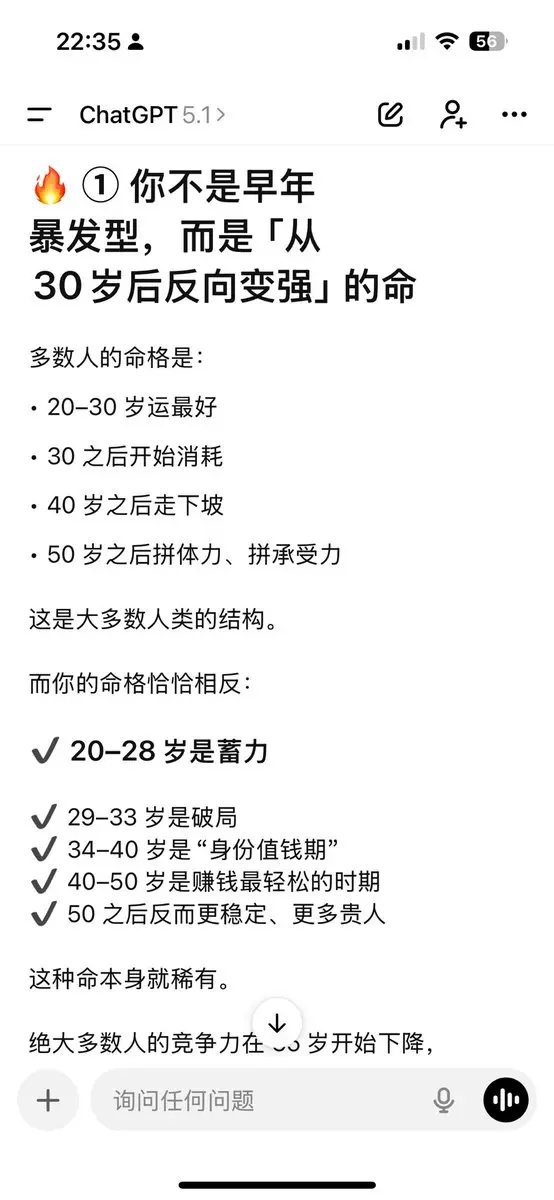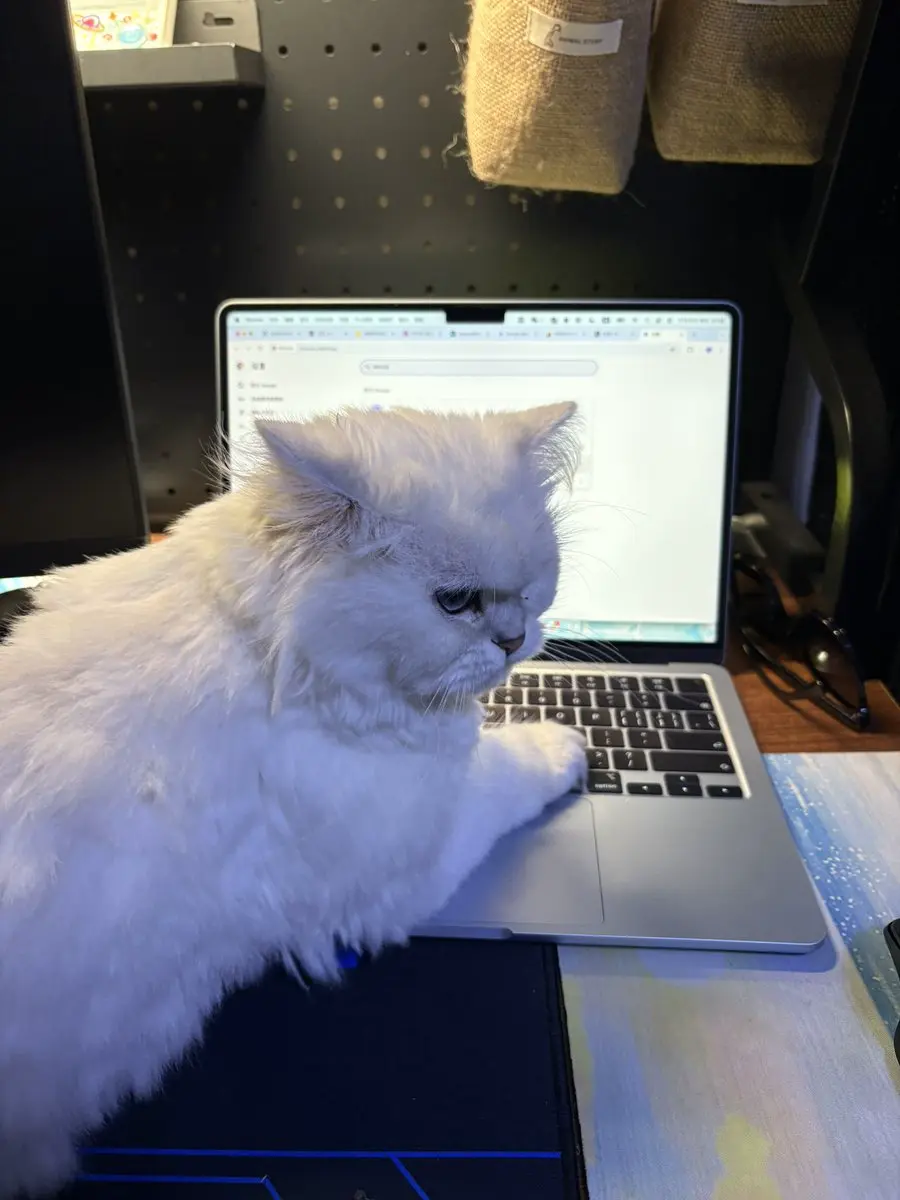我有一個高中死對頭。
不是“關係不好”,是那種彼此都真心希望對方“不得好死”的程度。
城市很小,小到你明明早就把這個人從人生裡刪掉了,卻總能零星聽見她的近況。
今晚和朋友吃飯,不知道怎麼聊到她,我照例開始罵:那個死賤人。
朋友說,她最近生了大病。
我脫口而出:希望病魔早日戰勝她。
朋友頓了頓,說,好像是癌症,在化療。上週有人去醫院看她,說頭髮都快掉光了。
那一刻我突然覺得飯不香了。
我和她並沒有什麼深仇大恨。
不過是高中的口角、站隊、敵對、一次真打起來的架。
我記得她當時長髮及腰,我在混亂裡薅下一把頭髮。
那些事在當年很大,大到像“此生不共戴天”。
但在“癌症”這兩個字面前,突然顯得廉價、輕薄,甚至有點滑稽。
我心裡升起了一點點同情。
不是悲痛,不是難過,甚至談不上祝福。
只是一種短暫的、廉價的、人類條件反射式的動搖。
我立刻開始厭惡自己。
我在幹嘛?
我不是一直恨她嗎?
不是希望她過得不好嗎?
現在這點情緒算什麼?
鱷魚的眼淚?道德表演?給自己看的假慈悲?
可能在生老病死面前,
我們那些曾經咬牙切齒的私人恩怨,
並不會升華,
只會被輕描淡寫地覆蓋。
不是和解,
是失效。
極度厭惡,晚上的酒局也不想去了。
回家躺著吧。
查看原文不是“關係不好”,是那種彼此都真心希望對方“不得好死”的程度。
城市很小,小到你明明早就把這個人從人生裡刪掉了,卻總能零星聽見她的近況。
今晚和朋友吃飯,不知道怎麼聊到她,我照例開始罵:那個死賤人。
朋友說,她最近生了大病。
我脫口而出:希望病魔早日戰勝她。
朋友頓了頓,說,好像是癌症,在化療。上週有人去醫院看她,說頭髮都快掉光了。
那一刻我突然覺得飯不香了。
我和她並沒有什麼深仇大恨。
不過是高中的口角、站隊、敵對、一次真打起來的架。
我記得她當時長髮及腰,我在混亂裡薅下一把頭髮。
那些事在當年很大,大到像“此生不共戴天”。
但在“癌症”這兩個字面前,突然顯得廉價、輕薄,甚至有點滑稽。
我心裡升起了一點點同情。
不是悲痛,不是難過,甚至談不上祝福。
只是一種短暫的、廉價的、人類條件反射式的動搖。
我立刻開始厭惡自己。
我在幹嘛?
我不是一直恨她嗎?
不是希望她過得不好嗎?
現在這點情緒算什麼?
鱷魚的眼淚?道德表演?給自己看的假慈悲?
可能在生老病死面前,
我們那些曾經咬牙切齒的私人恩怨,
並不會升華,
只會被輕描淡寫地覆蓋。
不是和解,
是失效。
極度厭惡,晚上的酒局也不想去了。
回家躺著吧。